追光文學巨匠 徐遲:勇當沸騰生活的記錄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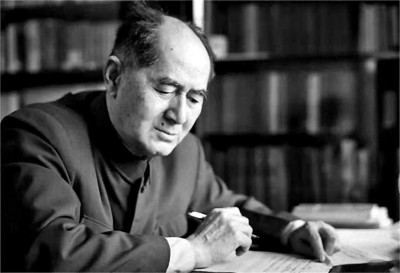
徐遲(1914—1996年)

1978年2月16日,本報頭版頭條轉載刊發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號召廣大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要刻苦學習,要研究新問題,要攀登科學高峰,要努力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自20世紀30年代踏上文壇開始,徐遲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還翻譯了不少外文作品。他的詩歌靈動多變,散文余韻悠長,譯文質樸典雅,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更是成為“科學的春天”的時代象征。
1963年3月,徐遲在《一些速記下來的思想》中寫道:“我們這時代的生活在沸騰。我們這時代的報告文學家是幸福的人,他們是這沸騰生活的見證人、記錄員。我們有過那樣的幸福的時刻,在手指握著筆管的時候,感覺到了我們的革命生活的脈搏。記得我曾睡在一個建設工地上,我以為我睡在共和國的跳動的心房上。”這是徐遲對自我的期許,也是他矢志不渝的藝術追求。回望徐遲豐富的創作生涯,他在做好沸騰生活見證人與記錄員時的一些思考和作為,具有特別的啟示意義。
“讓我們新詩人把想象的翅膀展開,并且拍擊起來”
徐遲是浙江南潯人,1914年出生,在家鄉度過了少年時代。1931年,他考入東吳大學文學院,主攻外國文學。1933年他進入燕京大學借讀,在冰心的詩歌課上,讀到了雪萊、拜倫和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詩,對詩歌的熱愛一發不可收。隨后,他開始在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上發表譯詩和詩評,并著手創作詩歌。受西方現代派詩人的影響,他在詩中注重意象的運用和主觀情感的表達,比喻新奇,詩句靈動活潑。他特別關注詩歌對現代都市文明的呈現,敏銳地觸及城市生活有關時間、工業文明與現代化的主題。比如,《都會之滿月》以“夜夜的滿月”對應“立體平面的機件”,發現月色下“短針一樣的人,長針一樣的影子”,借這類意象表現都市文明秩序下人類的生活體驗。
徐遲還將詩心寄托在鄉間月色和田園牧歌之中,以古典文學中的“月”“橋”“樹”等意象,表現閑適的生活節奏和溫情的鄉野體驗。在《春天的村子》《月明之村》《江南人》《故鄉》等詩作中,徐遲塑造了“河水之濱”小村莊和“劃著木船”的江南人,在如詩如畫的鄉村景觀和細膩豐富的日常節奏中,構建了江南故鄉的美好圖景,也寄托自己無限的依戀。
他的詩歌創作風格與時代的脈動保持一致。20世紀40年代,徐遲創作了《中國的故鄉》《歷史與詩》《誕生》《人民頌》等主題詩歌。50年代,他以《春天來了》《在明亮的陽光下》歌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盛況,“我聽見過煉鐵廠的熱風爐的呼嘯,也曾在天涯海角聽到過九級風咆哮,但國慶日的歡呼聲,蓋過了所有的那些聲音”。隨后他以記者身份,先后前往鞍山、長春、沈陽等重工業生產城市采訪,創作了一批寫實性的工業題材詩歌,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場景和經濟發展面貌。1957年,《詩刊》雜志創刊,臧克家任主編,徐遲任副主編,他將自己對詩歌的熱情投入刊物的編務工作中。
1979年2月,在一次詩歌創作座談會上,徐遲在發言時強調“詩是倚天長劍,詩是火把”,呼吁“讓我們新詩人把想象的翅膀展開,并且拍擊起來,為四個現代化歌唱而且戰斗,為四個現代化燃燒而且飛翔吧”。他以真摯的熱情和生命的激情,為當時的詩歌創作定下基調,描繪美好的發展藍圖。
“內容主要是新事物的報告,而形式卻是優美的文學”
徐遲一直對報告文學這個文體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他將報告文學視為“報曉”的、“曙光”的文學,認為報告文學“是新的文學,是美的文學,它是堅定信心的文學,它是純潔信仰的文學,它是崇高信譽的文學”。而他的作品也成為歷史發展進程和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見證。
1937年,他以親見親聞為素材,創作了《大場的一夜》《孤軍八百》等反映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作品。在20世紀50年代,他以武漢長江大橋建設為題材,創作了《漢水橋頭》《一橋飛架南北》《通車記》等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描繪了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場景和通車的雄壯景觀,塑造了數位橋梁工程師的形象,開啟了他對知識分子群體的關注。
在新時期,徐遲的創作進入高峰,推出《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在湍流的渦旋中》《生命之樹常綠》等一批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品。他重點關注自然科學領域,選取一批在學術上勇攀高峰、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如陳景潤、周培源、蔡希陶等,在深入采訪的基礎上,了解他們的研究內容和日常生活,力爭準確、全面地把握人物,進一步豐富了新時期文學的知識分子形象譜系,并且呼喚社會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強調知識與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發表于《人民文學》第1期。此時恰逢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這篇作品的問世掀起了一股熱潮,陳景潤也成為家喻戶曉的學習榜樣。《哥德巴赫猜想》聯通了新時期文藝的復蘇和科學精神的重建,為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奠定了整體性的創作基調。《哥德巴赫猜想》緊緊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重視科學事實的再現,也著力運用審美思維塑造人物形象。他大膽引用數學專業論文的部分內容,按說這是文學寫作的一個“禁忌”,但是徐遲的目的是展現科學家嚴密的邏輯推理,以陌生化彰顯科學知識的神圣性,同時又將數學論文進行形象化描述,“何等動人的一頁又一頁!這些是人類思維的花朵。這些是空谷幽蘭、高寒杜鵑、老林中的人參、冰山上的雪蓮、絕頂上的靈芝、抽象思維的牡丹”。
此后,徐遲的寫作轉向對具體科學知識的普及,寫下《雷電頌》《來自高能粒子和廣漠宇宙的信息》《計算機:迷人的精靈》等科普作品。他也關注宏觀層面的社會建設,推出了《刑天舞干戚——記葛洲壩》《汽車城觀感》《神“計”妙“算”小型機》等記述高新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作品。在他的筆下,科學與文學是相互貫通的,可以有機結合。而且,他始終以詩人的情懷和筆觸創作看似有些“生硬”的題材。1984年,在《報告文學的時代》中,他寫道:“報告文學的作者,既要寫出有豐富生活和深刻內容的歷史風貌來,并要寫得有光華四溢的藝術文采。”在他看來,報告文學“內容主要是新事物的報告,而形式卻是優美的文學”。在徐遲的作品中,事實性和審美性真正做到了彼此促進、相互融合。
“游記文學可以攀登哲學的高峰,思想的高峰”
徐遲對各種文體均有涉獵,除了廣為人知的報告文學和詩歌之外,還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小說、散文、雜文等。他的創作追求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內在一致,形成了富有個人風格的美學特色。
在徐遲的散文中,游記別具風格,既有寄情山水的《莫干山露營記》《大帽山紀游》,也有反映中國社會建設的《西行氣象萬千》《井岡山記》,更有兼具自然性和人文性的《法國,一個春天的旅行》《美國,一個秋天的旅行》。他在出游之前要進行許多準備,目的地的圖片、報道、地方志、地圖等,都是要精心收集的資料。他將撰寫報告文學時慣用的科學思想方法,也運用到游記的寫作之中,提出游記應該包含地理、氣候、風俗、文化等具體的科學記錄。他推崇《水經注》和《徐霞客游記》,希望能以準確的方式記錄山川大地,為后續科學研究工作的展開做足準備。
徐遲特別看重散文的思想性,推崇“文必以理為主,理亦因文而明”的創作態度,尤其欣賞魯迅的那些深刻、銳利的散文,認為其立“片言”而有“警策”,能夠發出為真理而斗爭的聲音。他撰寫游記,是為了情感的抒發,也是為了表達深沉的哲思,明確“游記文學可以攀登哲學的高峰,思想的高峰”。
打通小說和散文文體,追求風格、文采與思想的統一,這種開放的文體觀念在徐遲晚年的寫作中尤為顯著。他的自傳體長篇作品《江南小鎮》,以回憶錄形式展現了他個人的成長生活經歷,在歷史的波瀾中記述著自己的文學生命和革命生涯。這部作品規模宏大,將整個20世紀的歷史徐徐展開,人與事都凝聚在“水晶晶”的江南風景之中。那些有關戰爭、革命、自由、愛情的話題,與故鄉的愛戀凝結在一起,形成宏闊又悠然的審美體驗。徐遲的家鄉在浙江湖州南潯鎮,這是他人生的起點,也是他文學事業的起點。在《江南小鎮》的開篇,徐遲用66個“水晶晶”表達自己對故鄉純潔的眷戀之情:“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他從小鎮的歷史入手,將個人經歷與地域民俗緊密相連,用審慎和反思的眼光剖析歷史,以及自己的內心。他筆下的那些人和事,不僅是他個人的剖白,更是一代人真實的側影,呈現出動人而真誠的史詩特性。
“吸收中外文藝精華的總和”
在藝術觀念上,徐遲有著開闊的視野和包容的心態。比如,他鐘情以龐德為代表的意象派詩人,對艾略特、洛爾迦、里爾克等詩人也十分關注,曾經撰寫長文《意象派的七個詩人》介紹他們的詩歌主張。他寫道:“現在少有人再提出意象派來,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它也永遠不會消失了。有人說,自由詩解放了詩的形式,意象派卻解放了詩的內容。它是一次實驗,它解放了詩的形式和內容兩者。經過這個運動,詩開始在浩蕩的大道上前進了。”
他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始于讀書階段接觸的現代派作家,惠特曼、艾略特、海明威、里爾克等都是他的研究對象。徐遲還是一位重要的翻譯家,翻譯了雪萊、拜倫、海明威等眾多作家的作品,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系列作品和《托爾斯泰傳》也是重要的歷史文獻。
抗戰勝利后,鄭振鐸、夏衍等人策劃出版一套“美國文學叢書”,徐遲負責翻譯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在當時譯為《華爾騰》。據徐遲在《江南小鎮》中回憶,他在夏天著手翻譯《瓦爾登湖》,開始遇到了一點困難。后來,真切而又深沉的文本感染了他,他的翻譯工作愈發流暢,整個夏天都沉浸在寧靜而涼爽的湖畔風光之中。《瓦爾登湖》倡導自然樸素的生活態度,在美妙的風景描寫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內涵,這與徐遲的詩文創作風格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在序言中,他寫道:“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讀它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歡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么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么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可是黃昏以后,心情漸漸地寂寞和恬靜下來,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到了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之時,這《瓦爾登湖》毫不晦澀,清澄見底,吟誦之下,不禁為之神往了。”從這段敘述中可以看出,徐遲對這部作品飽含深情,事實是他的譯筆格調優美、意境豐富,具有音樂性和韻律美,受到翻譯界和讀者的一致認可,在數十年間不斷翻印,暢銷至今。
在徐遲看來,中國新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中外文學在交流、融合之中共同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寶庫。1978年5月,徐遲撰文祝賀《外國文學研究》季刊創刊,他主張“吸收中外文藝精華的全部總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拓寬我們自己的文學疆域。他坦言“外國的東西我看得很多,而且我承認,我是受外國文學培養的”,但他鮮明指出自己不愿意“做外國文學的俘虜”,而是要成為它的主人,“占有它,使它為我們服務”。
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徐遲堅持將時代的激蕩、生活的豐盈、文化的碰撞、心靈的寬闊和審美的趣味貫通起來。他在文體上不斷探索,追求風格的轉換,是兼顧創作、評論和翻譯等領域的“多面手”,為當代文學的豐富性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作者:劉陽揚,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