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女吊》:被發明的“復仇”與作為方法的“民間”
原標題:《女吊》:“故事新編”一種——被發明的“復仇”與作為方法的“民間”
作為魯迅生命末期的創作,《女吊》以其特殊的寫作時間和“朝花夕拾”風格的回歸在魯迅作品序列中引人注目。自作品問世以來,“民間”和“復仇”始終是解讀《女吊》題旨的兩個關鍵詞,作者對紹興目連戲中女吊復仇精神的稱頌,使人們再次辨認出那些“構成魯迅生命底蘊的童年故鄉記憶和民間記憶”[1],而魯迅精神結構的淵源之一,正是“那個在鄉村的節日舞臺上、在民間的傳說和故事里的明艷的‘鬼’世界”[2]。
無論從地域文化著眼還是借助“狂歡化”理論來解讀《女吊》,其論說均基于同一認識,即魯迅筆下之女吊乃以紹興目連戲中之女吊為藍本,基于此,《女吊》的回憶性散文屬性應該毋庸置疑。然而,如果對此前民間戲曲中的女吊形象進行一番“檢驗”,《女吊》的性質則變得面目可疑:在魯迅創作《女吊》以前,女吊并未以復仇者形象示人。也就是說,“復仇”主題實系魯迅之“發明”,而非植根于紹興民間戲曲舞臺。那么,《女吊》究竟是人們所說的“朝花夕拾”,還是另一種風貌的“故事新編”?真實存在于民間戲曲中的女吊應為何種面貌?魯迅“發明”的復仇精神,其具體指涉是什么?作者筆下的女吊形象是否另有靈感來源?其對民間資源的調用與改造又是在何種意義上進行的?
一
關于女吊故事本末,《魯迅全集》注釋如下:
楊家女:應為良家女。據目連戲的故事說:她幼年時父母雙亡,嬸母將她領給楊家做童養媳,后又被婆婆賣入妓院,終于自縊身死。在目連戲中,她的唱詞是:“奴奴本是良家女,將奴賣入勾欄里;生前受不過王婆氣,將奴逼死勾欄里。阿呀,苦呀,天哪!將奴逼死勾欄里。”[3]
這則注釋最早見于1958年《全集》,并在1981年和2005年版《全集》中延續使用,以解釋“奴奴本是楊家女”這句唱詞。然而考察各地目連戲抄本,女吊生前或是做媳婦,受公婆打罵,負氣懸梁;或是雙親亡故,賣入行院,最終自縊身死;并不見兩次被賣,先做童養媳后入妓院的說法。雖然民間目連戲版本眾多,留下文字的只是鳳毛麟角,不過從注釋所引四句唱詞來看,這則注釋的編寫卻并非依據某個秘而不傳的孤本,而只是紹興目連戲的一種常見版本。在現存各種目連戲抄本中,清代紹興敬義堂楊杏芳抄本(今亦稱《紹興舊抄救母記》)中的唱詞與此最為近似:“奴奴本是良家女,被人賣在勾欄里。生前受不過亡八氣,將身縊死高梁里。噯嚇苦嚇天那!將身縊死高梁里。”[4]此外,紹興地區其他版本,諸如新昌縣胡卜村清抄本《目連救母記》、新昌縣前良村清咸豐庚申年抄本《目連戲》、紹興民國九年齋堂本《救母記》等均與此大同小異,只有個別字句存在差異。1956年,前良目連班受邀赴上海參加“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演出”,趙景深將藝人攜帶的敬義堂楊杏芳抄本購入囊中,因此《舊抄救母記》成為1958年《全集》出版以前,眾多紹興民間目連戲抄本中唯一一個由知識分子收藏的版本。

趙延年木刻魯迅作品之《女吊》
《舊抄救母記》是否與《女吊》注釋有直接關系尚無從查證,但注釋者顯然參照了某個妓女故事版本。由于其與魯迅提供的童養媳一說無法匹配,于是采取了將兩種說法拼合的處理方法。實際上,童養媳版本在民間演劇中的確存在,1942年柯靈在文章里回憶他年少看戲時聽到的幾句唱詞:“奴奴本是良家女,從小做一個養媳婦,公婆終日打罵奴,懸梁自盡命嗚呼。”[5]不過其中“良家女”顯然與童養媳無關,只能源于妓女故事系統。一種可能是柯靈在1942年的記憶已被魯迅《女吊》“改寫”過,另一種可能是童養媳版故事晚于妓女版故事系統,而其唱詞直接在后者的基礎上重新加工。
不過就形象設定而言,童養媳故事顯然派生于更早的媳婦故事系統。稍早于魯迅寫作《女吊》,朱今曾于1934年發表《我鄉的目連戲》一文,紹介江蘇溧陽一帶目連戲的形態,尤其詳細記錄了“趕吊”一折的演出形式[6]。這一部分故事主要講述東方亮妻子獨自在家,因行善被騙去金釵,丈夫在外偶見金釵,遂疑妻子不貞,歸家詬誶,妻子無奈銜冤懸梁。一眾鬼魂聞訊來討替身,其中尤以吊鬼形象恐怖,正在她準備“討替”之際,王靈官出場驅趕吊鬼,東方亮之妻因此得救。這一故事模式廣泛存在于各地目連戲中,具體細節則因地而異,并無定章。但一個比較穩定的細節是吊死鬼的死因:因與公婆不睦而懸梁。然而,直到死后數十年她仍未能尋得替身,因此后悔當初氣量狹小,不能忍一時“閑氣”。在這一故事結構中,真正的主人公是投繯的婦人,而吊死鬼在劇中只須用一兩句話概述身世并自悔前番。在這里,吊死鬼幾乎不承擔藝術功能,而只負責兩項意義功能:就儀式而言,天神在故事結束時趕散冤鬼,以喻示地方安寧,是演出目連戲的主要目的。就世俗倫理而言,一方面,吊死鬼討替失敗,是為驗證“善有善報”,好人自有神明護佑的觀念,以達到勸善目的;另一方面,女吊以做鬼的凄涼景況現身說法,從而警誡輕生者。
紹興目連戲在“出吊”之前,也采用東方亮故事的基本情節,但在吊死鬼形象和演劇模式上自辟蹊徑,以男吊、女吊“爭替”取代眾鬼“爭替”。《男吊》一折無曲文,全靠男演員在一根懸空繩索上進行雜技表演,為紹興目連戲所獨創;女吊則從一眾冤鬼中提煉出來,成為完整獨立的形象,出現長達數百字的唱詞;同時擺脫先前的“無名”狀態,有了“玉芙蓉”的名字。其生前身份也不再是與公婆不睦的媳婦,而是命運凄慘的妓女。這一系統的女吊表演有四個清晰的層次,出場時,女吊玉芙蓉自述生平,講述幼年時父母亡故,被賣入勾欄,生意慘淡時屢遭鴇媽虐打,最終病臥床榻,于行將就木之際,被拋至荒郊。之后,女吊來到婦人房中,試圖引誘婦人上吊。繼而,婦人被救下,討替失敗的女吊面向觀眾,恫嚇世人須與人為善,不可輕生,否則自己便是下場。到了最后,女吊依例須被“打下臺”,完成“趕吊”儀式。這意味著,紹興女吊雖然發展為一個較豐滿的藝術形象,但其承載的勸善和禳災功能仍是這一形象的“立身之本”。
二
1990年丸尾常喜隨田仲一成率領的考察團赴浙江進行關于目連戲的調研,事后形成《浙東目連戲札記》。作為魯迅研究者,丸尾對《女吊》一出格外關注,他開始意識到:“不能說魯迅所介紹的老年人的說明明確了《女吊》《男吊》本來的意義。它們本來的意義大約與前面所述的朱今《我鄉的目連戲》所介紹的狀況相似。”[7]此時的丸尾清晰地界分了魯迅之女吊與目連戲之女吊。然而,在之后寫作《“人”與“鬼”的糾葛》時,這個界限卻重新模糊起來。他對魯迅小說的分析建立在目連戲的“原型結構”上,并指出:“要了解中國民眾的世界觀、生死觀,《目連戲》是很寶貴的資料。在對這散落、湮沒下去的《目連戲》的發掘、介紹工作中,魯迅占有重要的位置。”[8]這一復歸常識的結論最終封閉了其詳細考釋目連戲與“祖先祭祀”、“幽靈超度劇”關系后可能打開的闡釋空間。

紹劇《女吊》劇照
丸尾常喜的前后矛盾在于他是以兩種不同的身份進入兩個領域的研究,在以民俗采風者的姿態進入目連戲時,其思路與田仲一成一致,關注的是一般鄉民關于“鬼”的觀念,以及“目連戲”用以穩固包括家族、宗族在內的傳統社會關系的祭祀功能;而作為魯迅研究者時,他則指出魯迅的“孤魂野鬼”書寫表現了“對宗族主義邏輯的悲憤”[9]。就后者而言,丸尾的思路不是以民俗學的視角重釋魯迅,而是以魯迅思想來重釋民俗。其后果是魯迅對民俗的創造性書寫遭到遮蔽,與此同時,魯迅化了的民俗又反過來被視作影響過魯迅的某種精神傳統。如此,魯迅、民間、傳統三者間的關系仿佛清晰可辨,實則愈發混沌。
實際上,即使在《女吊》文本中,讀者也無法從女吊身上找到作者聲稱的那種復仇精神,這是魯迅無法跨越的敘事障礙。因此夏濟安很早就發現了《女吊》中的敘事縫隙和復仇說的杜撰性質:“這種復仇性其實是魯迅的一己之見,據他回憶,真正的表演中,女吊用哀怨的音調和可怕的動作,細述她以自殺告終的悲慘一生,隨后,當她聽見另一個準備自殺的女人的悲泣,不禁感到‘萬分驚喜’。”[10]也就是說,魯迅的“回憶”與“見解”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出入。回顧文本,《女吊》中言及復仇的幾次均系作者自行闡釋,與女吊本身無關。而《女吊》的“復仇”主旨乃由文章開篇強行定調:“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這意味著,《女吊》的復仇內涵與其說是由女吊這一民俗形象建構起來的,不如說是借由古典話語創造出來的。
魯迅引用這句話而非其他詩句辭章或更為相宜的民間諺語為“復仇”立論,恐怕并非隨機選擇。對于身處1936年的魯迅而言,這句名言不僅是一個遙遠的“典故”,同時也與彼時諸多文本和事件存在著某種互文關系。
背景一:
1936年前后,魯迅突然開始反復征引“會稽”一語,查《魯迅全集》可見三次,除《女吊》外,其余兩次均與一個叫黃萍蓀的人有關。2月10日,他在答復黃萍蓀約稿的信中寫道:
三蒙惠書,謹悉種種。但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系,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奉報先生殷殷之誼,當俟異日耳。[11]
大約同年,魯迅又作《關于許紹棣葉溯中黃萍蓀》(未刊)一文,言及他所了解到的黃萍蓀與官吏勾結,暗中撰文詆毀自己,并以此發跡之事:
當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時,浙江臺州人許紹棣,溫州人葉溯中,首先獻媚,呈請南京政府下令通緝。二人果漸騰達,許官至浙江教育廳長,葉為官辦之正中書局大員。有黃萍蓀者,又伏許葉嗾使,辦一小報,約每月必詆我兩次,則得薪金三十。黃竟以此起家,為教育廳小官,遂編《越風》,函約“名人”撰稿,談忠烈遺聞,名流軼事,自忘其本來面目矣。‘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然一遇叭兒,亦復途窮道盡![12]
文中“然一遇叭兒,亦復途窮道盡”一語,正可作《女吊》中“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但其實,是并不的確的”這個拗口句子的一個簡明注釋。兩次引用“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都與黃萍蓀有關,寫作《女吊》時一起手便拋出這句話,不會不想到他與黃氏間的這段“宿怨”。
1948年,黃萍蓀將魯迅復信的手稿公開,并撰文表示他見魯迅信后,便找浙江黨部熟人詢問通緝自由運動大同盟諸人一事,黨部人員回復并無此案;并稱自己后來還就此事與魯迅當面解釋清楚,已冰釋誤會[13]。黃萍蓀的說法未必足信,早在1935年,他就曾寫過《雪夜訪魯迅翁記》,杜撰了他與魯迅的會面,這一點他在后來也私下承認過[14]。此番是否故技重施不得而知,但魯迅說的“辦一小報,約每月必詆我兩次”應該也是道聽途說,否則不會知道“薪金三十”這樣的幕后細節;此外,目前也沒有資料顯示黃萍蓀曾經辦過詆毀魯迅的“小報”。至于魯迅此文寫就后留在手里不發,不知是否由于還未完全確證文中提到諸人諸事的真實性。
不過這里要談的問題不在于黃萍蓀是否當面與魯迅澄清過此事,也不在于黃萍蓀是否蒙冤,而是與“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這句為《女吊》全篇奠定基礎的引語真正形成互文關系的,并非鄉間的女吊形象,而是與《越風》編輯、“教育廳小官”黃萍蓀有關的一信一文。
背景二:
早在1925年,《語絲》上曾登載過一封桑洛卿給周作人的信,周作人進行回復,兩封信以《鄉談》為題刊登。在復信中,周作人也使用了“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一語。需要提醒的是,這句話在王思任的《讓馬瑤草閣部》中原作:“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15]他在文中怒斥馬士英擁立福王后竟“兵權獨握”,尤為人不齒的是“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最后更以越鄉民眾的復仇精神恫嚇馬士英,逼其自裁以謝天下。從周作人和后來魯迅所引的異文來看,他們最初見到的并非《讓馬瑤草》原文,而是清末李慈銘在《越中先賢祠目序例》中對王季重其人其文的稱贊:“檄馬士英一書正氣凜然,其云‘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地’二語尤足廉頑立懦,景仰千秋。”[16]1928年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再次征引這句話:“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有些人終于做了忠臣,如王謔庵到復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的話,大多數的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17]仍然強調了“隱遁”下實為“反抗”。及至1934年周作人作《<文飯小品>》,再度提及王思任致馬士英書時,卻已是另一種看法:“此文價值重在對事對人,若以文論本亦尋常,非謔庵之至者,且文莊而仍‘亦不廢謔’。”[18]已在強調反抗色彩之下仍不能掩的“謔”,這無疑是在與“載道派”對壘。1936年9月16日,即魯迅開手作《女吊》的三天前,周作人致林語堂的一封信刊載在《宇宙風》上,稱“近日擬寫一小文,介紹王季重之《謔庵文飯小品》,成后當可以寄奉,此書少見,今年以屠隆之《棲春館集》一部易得之者也”,頗有珍重之意。信末又以明末比附當時,以為“虜患流寇,八股太監,原都齊備,載道派的新人物則正是東林,我們小百姓不能走投其中某一路者活該倒楣。”[19]很長一段時間,周氏文末都像這樣,每每須與載道派交鋒一番,使其“謔”的趣味顯得格外沉重。其實,言志也好,載道也罷,當魯迅在生命末期不斷使用這句周作人曾反復征引的“改造”后的鄉賢名言,不僅是兄弟二人曾經共享同一傳統知識資源的見證,更是時空相隔下,兩人從同聲相應走向各言其志的一場頗具象征意味的潛對話。
更重要的是,當魯迅反復征引王思任的“報仇雪恥”之言時,“晚明小品熱”正逢其盛,而王思任正是被大力推崇的一位。1932年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沈啟無編選的《近代散文抄》,選入王季重小品文16篇,數量上僅次于袁中郎、李長蘅、張宗子,內容幾乎均為游記。1935年,施蟄存更是直接借用王思任《文飯小品》之名,在上海創辦新刊。同年他又主編了“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雖云“中國文學”,而公安、竟陵兩派分量極重,《王季重十種》亦入選其中,由阿英校點。這年年底,魯迅作《雜談小品文》,提及“今年又有翻印所謂‘珍本’的事”時有這樣的評價:“現在只用了一元或數角,就可以看見現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床架屋,現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20]直把古人今人一網打盡。不過魯迅所非議者并非“小品文”或“性靈”本身,而是“獨尊”之態:“雖說抒寫性靈,其實后來仍落了窠臼,不過是‘賦得性靈’,照例寫出那么一套來。”而“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灑脫,無清初的所謂‘悖謬’”[21]。這本質上是在談“性靈”作為“一是之學說”的虛偽性。在此前所作的《“招貼即扯”》中,他更是舉出袁中郎如何服膺具有“方巾氣”的顧憲成作為實例,說明小品文的師祖也并非只有一張面孔、只貫徹一種主張[22]。而到《女吊》時,魯迅基本采取了相同“策略”,他對王思任“會稽”一語的征引,擊中了晚明小品推崇者對王思任其人其文“謔”與“性靈”的單一面向的言說,翻檢出其極具“方巾氣”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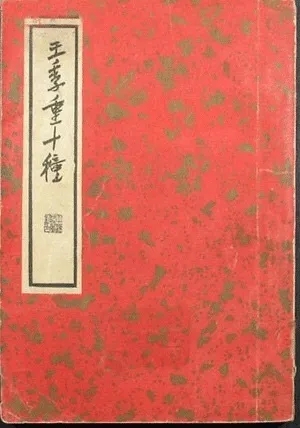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之《王季重十種》
不難看出,無論是與黃萍蓀在現實生活中的恩怨,與周作人自覺或不自覺的潛對話,還是與晚明小品文推崇者的觀念交鋒,“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都去民間女吊形象遠矣,而指向了魯迅與知識界的多方糾葛,潛藏著真正的“民間”大眾無從了然的用心。這是面向知識分子的發難,而非向著“鄉土中國”的發聲。
三
《女吊》中魯迅對“復仇”的贊頌是熱烈的,這種態度同樣見于《鑄劍》《復仇》等作品中,但不應忘記,很多時候他卻對“復仇”采取一種否定性書寫。未莊鄉民用“燈”和“亮”的“禁語”取笑阿Q時,他“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你還不配……’。”被革命軍拒絕后,阿Q“對于自己的盤辮子,仿佛也覺得無意味,要侮蔑;為報仇起見,很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但也沒有竟放。”這里,復仇心理被魯迅納入國民性批判敘事。消除了《阿Q正傳》的戲謔筆調,《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則正面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說在中國的社會上,人們“大抵無端的互相仇視……我因此對于中國人愛和平這句話,很有些懷疑,很覺得恐怖”[23]。1925年寫就的散文《頹敗線的顫動》和小說《孤獨者》中重復閃現著同一個場景,孩子手持蘆葉,向人喊“殺”。這種人性中自帶的仇恨“種子”,使魯迅和他筆下的人物都感到莫大的驚懼,魏連殳終于“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以此作為復仇——一種綏惠略夫式的復仇。1926年魯迅談及綏惠略夫時表示“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24]無論是阿Q式的復仇,還是綏惠略夫式的復仇,都為魯迅所反對。因此辨明魯迅在不同語境中的“復仇”話語是必要的,也就是說,真正的問題不在于魯迅是否主張復仇,而是他主張的是何種復仇。
魯迅的復仇書寫可以追溯回早期的《摩羅詩力說》,在這篇論文中,他稱拜倫“復仇一事,獨貫注其全精神”[25];“懷抱不平,突突上發,則倨傲縱逸,不恤人言,破壞復仇,無所顧忌,而義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并著意提醒:“若為自由故,不必戰于宗邦,則當為戰于他國。”[26]即復仇并非民族主義式的,而是為自由之戰,或者說,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那么,魯迅對拜倫以及此后密茨凱維支等人“復仇”精神的稱頌,是相對何種觀念而言的?他在文中也做出了解釋:
人人之心,無不泐二大字曰實利……夫心不受攖,非槁死則縮肭耳,而況實利之念,復姑黏熱于中,且其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則馴至卑懦儉嗇,退讓畏葸,無古民之樸野,有末世之澆漓。[27]
以此反顧中國,他指出中國文化的缺點正在于“以孤立自是,不遇校讎,終至墮落而之實利”[28]。也就是說,魯迅試圖宣揚的“復仇”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的、去功利性的復仇,要求摒除對復仇以后的“實利”的謀求。
實際上,這種純潔的復仇觀其來有自,章太炎曾作《復仇是非論》強調“人茍純以復仇為心,其潔白終遠勝于謀利”[29],魯迅對理想復仇的闡釋與此相通。不過,章太炎把“復仇”視作“排滿”的一部分,因此他一開始就提出:“今以一種族代他種族而有國家,兩種族間其豈有法律處其際者,既無法律,則非復仇不已。”[30]顯示出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而“復仇”之后,他提出了下一步建設性對策:“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則政治易以精嚴,于是解仇修好,交相擁護,非獨漢家之福,抑亦滿人之利。”[31]即借助復仇手段,最終要達到的是各民族“解仇修好”之旨歸。而章太炎一直強調的“民族主義”僅作為一項策略提出,不具終極性,他說:“舉其切近可行者,猶不得不退就民族主義。”[32]既然“民族主義”只是一種政治方案,那么其哲學底色又是什么?章太炎在文末做出這樣的自白:“人我法我,猶謂當一切除之。”[33]對“人我法我”的破除在此后的《建立宗教論》中又得以深化,即建立“以自識為宗”的新宗教,章太炎進一步闡釋:“識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34]“圓成實性”是印度唯識學和中國法相宗所說的“三性”之一,與“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相對。“遍計所執自性”是觀念的產物,離開意識便不具意義,比如“色空”“自他”“內外”等概念;“依他起自性”則指一切依因待緣之現象,而“逮其證得圓成,則依他亦自除遣”[35]。章氏的“真如”哲學主張“無量固在自心,不在外界”,但“自”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我”,而是“特不執一己為我,而以眾生為我”[37]。因此,章太炎是把復仇視作最初級階段的“行動”,而最終要去除“人我法我”以抵達“真如”境界。
章氏意在以“復仇”之術求“真如”之道,這種術道相離、體用二分的做法本身就充滿危險。在魯迅這里,“復仇”則被賦予本體性,而不僅充當一項政治實踐。章太炎對“復仇”之后的構想是“解仇修好”,魯迅卻說“平和為物,不見于人間”。至于政治上,魯迅則指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詩人卻正是觸犯這一禁忌的“攖人心者”,“其聲激于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37]。魯迅無意于將“復仇”滯留于“民族主義”立場,而使其超越實在的行動,并進入抽象的精神力量和審美資源層面,即“攖人心”。因此與章太炎把復仇寄托于革命不同,魯迅更傾向于將復仇寄托于文藝,他一方面作《摩羅詩力說》稱頌拜倫譜系文學家的“摩羅精神”,一方面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展示這種復仇精神,《復仇》中一男一女“持刀對立曠野”卻“也不擁抱,也不殺戮”,以最大的無聊向看客復仇;《復仇(二)》中被凌辱的“神之子”因悲憫人們的前途,而仇恨人們的現在;直到《鑄劍》,黑色人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復仇表現到近乎極致。
這種復仇觀的困境在于它只能停留在精神層面,而無法通向“動作”之“旨歸”,否則極易滑向阿Q式復仇或綏惠略夫式復仇,即魯迅自己反對的內容。這也造成了《女吊》的敘事障礙——“討替代”作為傳統女吊形象的核心行動無法直接過渡為“復仇”,作者更是特意區隔了復仇與討替代的意義:“中國的鬼還有一種壞脾氣,就是‘討替代’,這才完全是利己主義”,“習俗相沿,雖女吊不免,她有時也單是‘討替代’,忘記了復仇。”這樣敘事的后果是作者只能指認女吊為復仇者,卻無法提供女吊復仇的實例。
四
以“單是‘討替代’”而“忘記了復仇”的女吊作為復仇精神的代表,其說服力顯然不足。那么這一存在天然“劣勢”的形象為何仍能被魯迅納入其復仇書寫序列?
事實上魯迅關于女吊的印象應該并未落在童年時故鄉的戲臺上,而很可能來自于多年后陶元慶的畫作《大紅袍》。1925年魯迅在陶元慶的個人展覽上見過這幅畫后,即與許欽文商議:“《大紅袍》,璇卿這幅難得的畫,應該好好地保存。欽文,我打算把你寫的小說集結起來,變成一本書,定名《故鄉》,就把《大紅袍》用作《故鄉》的封面。這樣,也就把《大紅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來了。”[38]本應起輔助作用的封面畫,這時卻有些“喧賓奪主”的意思,足見魯迅珍重之意。

許欽文《故鄉》封面
作為陶元慶的好友,許欽文見證了《大紅袍》的整個創作過程:
(陶元慶)當時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里,日間到天橋的小戲館去玩了一回,是故意引起些兒童時代的回憶來的。晚上困到半夜后,他忽然起來,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一口氣畫就了這一幅。其中烏紗帽和大紅袍的印象以外:還含著‘吊死鬼’的美感——紹興在演大戲的時候,臺上總要出現斜下著眉毛,伸長著紅舌頭的吊死鬼,這在我和元慶都覺得是很美的。[39]
陶元慶還向許欽文闡述過創作中一些更具體的想法:
《大紅袍》那半仰著臉的姿態,當初得自紹興戲的《女吊》,那本是個‘恐怖美’的表現,去其病態的因素,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神情:悲苦、憤怒、堅強。藍衫、紅袍和高底靴是古裝戲中常見的。握劍的姿勢采自京戲的武生,加以變化,統一表現就是了。[40]
兩人的說法基本還原了創作的三個步驟,首先,《大紅袍》是從紹興戲劇中的女吊取材,構成畫面主體;其次,畫家在女吊原型的基礎上濾去了原有的病態之恐怖,而著力塑造“悲苦、憤怒、堅強”的神情;最后,在外形設計上吸納了京劇元素,這主要體現在大紅袍和厚底靴等行頭以及武生的握劍姿勢上,這一切都帶有典型的男性印記,而這一陽剛化改造正是去除女吊原型病態因素的重要環節。經過陶元慶改造的女吊和后來魯迅筆下的女吊給人的印象幾乎一致,只是《大紅袍》僅凸顯女吊的“悲苦、憤怒、堅強”,還未發展為魯迅反復強調的“復仇”。
但魯迅很可能已經從《大紅袍》那里誤讀出“復仇”精神。他對《大紅袍》的傾心無關于其女吊的選材,而主要來自畫面中“劍”的意象,他向許欽文稱道:“璇卿的那幅《大紅袍》,我已親眼看見過了,有力量;對照強烈,仍然調和,鮮明。握劍的姿態很醒目。”[41]據許欽文回憶,魯迅后來專門寫信給陶元慶,告訴他“有個德國的美術家叫Eche的也說《大紅袍》很好,劍的部分最好”[42]。無論是魯迅自己的評價,還是向畫家轉述別人的評價,都對“劍”的意象給予格外關注。可以說,“劍”是魯迅通向《大紅袍》的理解之門。而綜觀魯迅的復仇書寫,“劍”幾乎可以視作其核心審美意象,《鑄劍》毋庸置言,《摩羅詩力說》中言及拜倫處多次出現“孤舟利劍”意象,《復仇(二)》中赤裸的兩人也“捏著利刃,對立于廣漠的曠野之上”……魯迅將復仇的審美想象凝結在劍意象中,而陶元慶的畫中之劍很可能觸發了魯迅的心中之劍,這為魯迅日后把女吊形象與復仇精神關聯起來提供了重要的藝術資源。
1924年,魯迅譯作《苦悶的象征》的封面亦出自陶元慶之手。陶元慶到北京后不久,許羨蘇即在魯迅處提及此人。魯迅又向許欽文詳細詢問了陶元慶的情況,對其繪畫風格有了基本了解后,便托請許欽文邀他為《苦悶的象征》繪制封面,這是兩人多次合作中的第一次。封面的基本構想是頭發蓬亂的少女舔舐手中的一柄镋叉,所有元素均由曲線線條抽象凝練而成,包孕在圓形輪廓中,融入日本圖案風格,頗具象征意味;色彩主要由黑、藍、紅三色構成,對比度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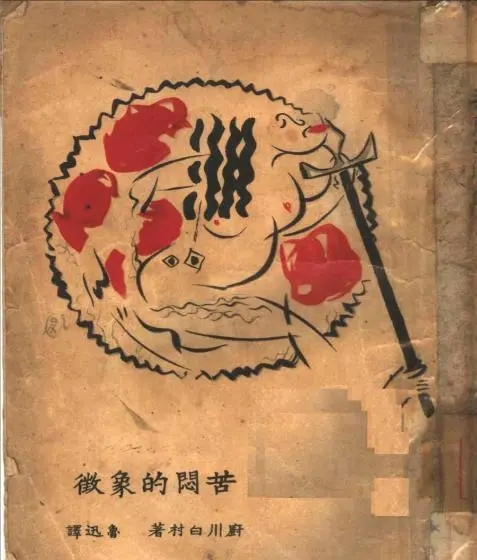
魯迅譯《苦悶的象征》封面
有意思的是,對比《大紅袍》和《苦悶的象征》封面,兩幅畫的基本元素和用色如出一轍,散發的女子,寒氣凜凜的兵器,黑、藍、紅的配色,幾乎可以把《苦悶的象征》看作高度抽象化之后的《大紅袍》。陶元慶較少自我重復,這兩幅畫的內在聯系不言而喻。在魯迅那里,雖然《大紅袍》的創作早于《苦悶的象征》封面,但魯迅先見到的卻是后者,這不僅為魯迅后來鑒賞《大紅袍》提供了理解的“前結構”,也為魯迅重新想象女吊形象,為之灌注個人化隱曲提供了途徑。
五
雖然魯迅的女吊印象極可能受到《大紅袍》影響,但在作品中他仍舊將其復歸于民間社戲舞臺上。實際上,魯迅雖然在《社戲》《無常》《女吊》等作品中一再表達對于社戲的傾心,但其童年時代真實的觀劇體驗卻未必像文學作品中敘述的那樣。在《偶成》里他透露了關于社戲的另一種記憶:“前清光緒初年,我鄉有一班戲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實不符,戲做得非常壞,竟弄得沒有人要看了。”[43]這提示我們,日后魯迅對社戲的欣賞并非看重其本身,而是看重其觀念意義上的闡釋空間。
早在1908年所作的《破惡聲論》中,魯迅已經擺明捍衛社戲的態度:
若在南方,乃更有一意于禁止賽會之志士。農人耕稼,歲幾無休時,遞得余閑,則有報賽,舉酒自勞,潔牲酬神,精神體質,兩愉悅也。號志士者起,乃謂鄉人事此,足以喪財費時,奔走號呼,力施遏止,而鉤其財帛為公用。嗟夫,自未破迷信以來,生財之道,固未有捷于此者矣。夫使人元氣瘰濁,性如沉鞠;或靈明已虧,淪溺嗜欲,斯已耳;倘其樸素之民,厥心純白,則勞作終歲,必求一揚其精神。故農則年答大戩于天,自亦蒙庥而大嵩,稍息心體,備更服勞。今并此而止之,是使學軛下之牛馬也,人不能堪,必別有所以發泄者矣。況乎自慰之事,他人不當犯干,詩人朗詠以寫心,雖暴主不相犯也;舞人屈申以舒體,雖暴主不相犯也;農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則志士之禍;烈于暴主遠矣。[44]
他在這里指出,禁止賽會的“志士”們本著經濟的需求、功用性的觀念,否認人的超越性精神需求,這是對人類精神的暴政,比獨夫之暴政更甚。因此,魯迅將“志士”斥為“偽士”,稱其“借口科學”不過“拾人余唾”,實則對“科學何物,適用何事,進化之狀奈何,文明之誼何解”不明就里。如此,被宣揚的“科學”已非科學本身,而是一個概念空殼。在《科學史教篇》里,他更清晰地表述了“科學”能與時俱進,而非一定之規。當“科學”成為“一是之學說”的知識話語,即取得統馭社會、“以眾虐獨”的權力。正是基于對話語權力的抵抗,或說出于“偽士當去”的訴求,使得“民間”資源在魯迅那里獲得了“意義”。
但“民間”本身在魯迅看來并不可靠,這從魯迅對京劇的態度即可見出。社戲和京劇均植根于民間社會,但魯迅對二者的評價判若云泥。一方面,社戲和京劇雖然都是民間大眾的藝術,但卻屬于兩個不同的“民間”世界,從《社戲》中我們可以理解魯迅是將京劇放置在現代市民社會中來打量的,而社戲則屬于前現代的鄉土社會,但只有后者可以獲得“民間”的稱謂——五四以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民間”的發現正是沿此思路展開。在這一思路中,“民間”并不處于建構中的“當下”,而被視作已完成的實體,它本身不具自足性,而是作為抗衡官方社會和主流傳統的“他者”被想象與征用。另一方面,魯迅否定京劇的原因已經在批評梅蘭芳時說過:“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著他們滅亡。”[45]魯迅深諳此“民間”的不穩定性及不可靠性,這意味著他對“民間”資源和“民間”概念的頻頻征用,實際只是將“民間”作為方法,而非立場。
那么,魯迅的“立場”,或說最終要求是什么?這需要溯回他在《破惡聲論》中提到的兩個核心概念:“心聲”和“內曜”。“內曜者,破瘰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其真義在破除“他信”以重建“自信”。而其所謂“迷信可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夫神話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則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異,淑詭可觀,雖信之失當,而嘲之則大惑也。”[46]這意味著他看重的是“迷信”表象下的“神思”,即太古先民不因襲“他信”的想象力。多年后,魯迅翻譯《苦悶的象征》,亦可視作對其早年論述的接續,在《苦悶的象征·引言》中,魯迅把翻譯他人著作時“壓在紙背的心情”亮明在紙面上,他直言:“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但中國現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錮蔽呢?”[47]
不過他又進一步解釋,對“心聲”和“內曜”的激發卻“不大眾之祈,而屬望止一二士,立之為極,俾眾瞻觀。”[48]即不能依靠民間大眾,而須依靠少數幾個人來為大眾示范。因此,通常意義上的重啟民間資源以破壁固化的精英社會或官方社會于魯迅而言僅是具備可操作性的第一步,其核心卻恰是反面,即對“一二士”——那些有能力對世俗“精英”和士大夫傳統進行清掃、并重新激發人的上古天然之心的人——的吁求,而此中蘊含的實為更具理想色彩的精英意識。
如此,我們得以理解,“民間立場”作為一種策略性話語使得女吊成為可資征用的形象;“精英意識”卻使作者對女吊不得不進行一場根本性重塑,使其由一個承載勸善與宗教祭祀功能的傳統民俗形象轉為向“他信”的知識權力和話語權力“復仇”的文學資源。至于從《無常》到《女吊》,魯迅對古老目連戲中那些鬼魅的念念不忘,正是為其“逞神思而施以人化”的古異淑詭所吸引。從鬼魅書寫中滲透出的苦悶與寂寞,更是作者無以為外人道的“象征”之所系。
注釋:
[1] 錢理群:《魯迅筆下的鬼——讀<無常>和<女吊>(二)》,《語文建設》,2010年第12 期。
[2] 汪暉:《“死火”重溫——以此紀念魯迅逝世六十周年》,《天涯》,1996年第6期。
[3] 《魯迅全集》第6卷,第6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4] 參見徐宏圖校訂:《紹興舊抄救母記》,第166頁,臺灣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7年版。
[5] 柯靈:《神·鬼·人——戲場偶拾》,《萬象》第2卷第8期,1943年2月1日。
[6] 參見朱今:《我鄉的目連戲》,《太白》,第1卷第8期,1935年1月5日。除紹興外,各地目連戲抄本中,保留出吊情節的基本屬于這一故事系統。目前公開印行的版本還有安徽:皖南高腔目連卷、池州東至蘇村高腔目連戲文穿會本、池州青陽腔目連戲文大會本;江蘇:超輪本目連(高淳陽腔目連戲三本目連演出本);湖南:辰河高腔目連全傳、湘劇大目犍連等(辰河高腔本和湘劇本無“趕吊”儀式)。以上可參見王秋桂主編“民俗曲藝叢書”。此外,清乾隆間,宮廷文人張照奉旨編纂《勸善金科》,東方亮妻子自縊故事置換為女子守節自盡,鬼魂爭替部分取消“趕吊”儀式,宮廷演劇意在強化目連戲道德勸誡功能,鄉間以演劇行鬼魂祭祀之風彼時恰為官方所禁除。參見張照編寫,詹怡萍校點:《清代宮廷大戲叢刊初編·勸善金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7] [日]丸尾常喜:《浙東目連戲札記》,壽永明、裘士雄主編:《魯迅與社戲》,第20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9] [日]丸尾常喜:《“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第34頁、第2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10]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陰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37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1] 魯迅:《360210致黃蘋蓀》,《魯迅全集》第14卷,第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12]魯迅:《關于許紹棣葉溯中黃萍蓀》,《魯迅全集》第8卷,第4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13] 參見黃萍蓀:《魯迅與“浙江黨部”之一重公案》,《子曰叢刊》第2緝,1948年6月10日。
[14] 1981年倪墨炎當面向黃萍蓀求證《雪夜訪魯迅翁》一文是否虛構,黃萍蓀也承認了“這篇文章有招徠讀者之心”,同時申明“但實在不存攻擊魯迅之意。我編刊物,很希望魯迅能寫稿,怎么會去攻擊他呢?”參見倪墨炎:《也談黃萍蓀與魯迅》,《文匯讀書周報》,1997年1月4日。此外,謝其章認為黃萍蓀不僅《雪夜訪魯迅翁》一文是虛構,后來《魯迅與“浙江黨部”之一重公案》中關于與魯迅會面,消釋誤會的記述也可能處于杜撰。參見謝其章:《黃萍蓀到底見過魯迅沒有?》,《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
[15] 李漁輯:《尺牘初征》卷一,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16] 李慈銘:《越縵堂文集》卷十二,第8頁,民國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17]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第180頁,北新書局1929年版。
[18] 周作人:《文飯小品》,《人間世》9期,1934年8月5日。
[19] 《知堂先生近影及手札》,《宇宙風》25期,1936年9月16日。
[20][21] 魯迅:《雜談小品文》,《魯迅全集》第6卷,第432頁、第4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22] 參見魯迅:《“招貼即扯”》,1935年2月20日《太白》1卷11期。
[23] 魯迅:《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24] 魯迅(向培良記):《記魯迅先生的談話》,《語絲》第94期,1926年8月28日。
[25][26][27][28][37]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78頁,第82頁,第71頁,第101頁,第7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29][30]]32][33] 章太炎:《復仇是非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80頁,第277頁,第282頁,第28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1] 章太炎:《排滿平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4][35][36] 章太炎:《建立宗教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436頁,第436頁,第4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8][40][41][42] 許欽文:《魯迅和陶元慶》,《〈魯迅日記〉中的我》,第86頁,第86頁,第86頁,第8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9] 許欽文:《陶元慶及其繪畫》,《人間世》第24期,1935年3月20日。
[43] 魯迅:《偶成》,《申報·自由談》,1933年6月22日。
[44][46][48] 魯迅:《破惡聲論》,《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5日。
[45] 魯迅:《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中華日報·動向》,1934年11月5日。
[47] 魯迅:《苦悶的象征·引言》,第3頁,北新書局1925年版。
(轉載自“文藝批評”微信公眾號)


